风暴中的骑手:移民营地的生活

在驱车前往大合成难民营的途中,我们经过一个公交车站,车站周围聚集了50多人。他们正在等待前往海滩的公共汽车,在那里他们将会见人口走私者,并试图登上开往多佛的臭名昭著的“小船”。
敦刻尔克郊区的格兰辛特是那些在英国寻求新生活的人的最后一站,尽管对一些人来说,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站。9月3日,12人在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时丧生。其中一半是儿童。这使得今年的死亡人数达到21人。
新任内政大臣伊维特·库珀(Yvette Cooper)表示,工党正在履行减少越境人数的承诺,报告称“进展令人鼓舞,在欧洲查获了大量船只和设备”。政府夸耀称,8月份查获了40起偷渡的小船引擎。
然而,截至9月初,已有2.2万名寻求庇护者在2024年穿越边境,而政府尚未任命一名边境安全指挥部负责人,该负责人将制定一项战略,以履行基尔·斯塔默(Keir Starmer)粉碎帮派的承诺。
与此同时,人口走私者变得更加大胆,他们拥有更大的船只,可以把更多的人装上船,以弥补缉获的人口。他们的客户不断抵达大synthe和加莱的临时营地,准备冒着生命危险。
在我们前往营地的路上,随时都有350到800名寻求庇护者聚集在这里,狭窄的道路穿过被死水运河包围的田野。地平线上到处都是工厂,把缕缕蒸汽喷向天空。到处都是平坦的绿色。
我在慈善机构Roots的同事注意到公交车站的人群后,就发了一条信息,提醒另一家告诉人们过马路危险的慈善机构。他们还建议如何穿上救生衣,以及如果在海上发生意外应该拨打什么紧急电话。
这个群聊还允许志愿者分享安全问题。他们面临着来自警察的危险,警察以使用高压水枪、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而闻名,有时,当营地的派系和等级之间的冲突过于激烈时,他们也会受到其他移民的威胁。
弹出一条信息:“安珀警告”——这意味着不需要志愿者撤离,但警惕程度很高。另一条消息如下:“营地远处传来枪声。不必惊慌。”
我被告知不要太担心警察。“他们通常不打扰我们,”一名志愿者解释说,“因为我们是做水的。”
我将花三周时间为Roots做志愿者,该组织于2017年在加来的一间卧室里成立,用旧笔记本电脑电池为生活在难民营的人制造充电宝。这是改革派议员李·安德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贬低的慈善机构之一,他的部分内容是:“我们在加来的英国慈善机构鼓励这些非法移民进入他们的营地,在那里他们提供住所、食物、给他们电话、数据,并教他们说英语。”
另一种观点是,在整个悲惨的过程中,慈善机构是唯一将移民视为人的机构。一名工人告诉我:“我们说‘难民’这个词,它就像一个脏话一样传开了。”“我们没有看到更大的图景。”
这就是Roots想要做的。在大流行期间,敦刻尔克的一次警察驱逐导致数百人流离失所,无法获得饮用水。树根填满了缝隙,散发出数千升的水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国家建立了公共水龙头,根继续维护和补充自己的大容器,每个可以容纳1000升水。现在,数百名志愿者为每年经过“大合成”的数千人提供电力、水、淋浴、洗漱用品,并组织食物分发。
一些志愿者穿着印有帕丁顿熊形象的t恤,上面写着“移民不是犯罪”的口号。我也看到很多咖啡杯上都有;这也概括了移民们所处的困境。他们是逃离真正危险的人——2022年,只有24%的庇护申请被拒绝,而在反对该决定的上诉中,85%的人被推翻。然而,他们在法国面临敌意,甚至身体上的暴力,而那些到达英国的人往往不得不面对一个“敌对的环境”。
慈善工作者知道如何让事情变得更好——安全、合法的路线;在法国建立更多的基础设施,以便在那里处理移民;一旦难民的申请获得批准,一个更清晰的系统来帮助他们进入英国生活,而不仅仅是把他们扔在酒店里。
一名工人说:“我环顾营地,看到的人可能是我的妹妹、女儿、父亲——他们可能是我。”
我们开始建立Roots最有价值的项目之一:社区中心。凉亭为配有电源插座的长桌子遮荫。人们向插座走去,把充电器伸到前面。
今天,我们有足够的出口。昨晚,六艘船渡了海。
我所看到的“营地”并不是我所期望的;由于法国警方不再允许正式的营地,他们会破坏任何建立永久定居点的企图,大synthe实际上只是人们躲在森林里,就像这里以西40公里的加莱营地一样。
我们的活动重点是“分发点”,即位于高速公路和铁路之间的停车场的分发点。很难说我们离海岸只有几公里了。洗过的金雀花丛是最近的天然遮荫源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开始对地理有了大致的了解,也对营地里不同的社区有了大致的了解:苏丹区、库尔德区、越南人区。
在另一张桌子上,艾米莉亚展开多米诺骨牌,连接4。我打开一袋叠叠玩具。一群苏丹人,又高又瘦,缓步走来。他们向艾米莉亚打招呼。她做志愿者已经三个星期了,认识很多志愿者。她会说一点男人的语言。
他们一起开玩笑,评估她在两周的指导下学会了多少多米诺骨牌策略。一个人带来了一顶巨大的太阳帽。他在帐篷里绕来绕去,让同伴们试穿。
艾米莉亚轮到她了。“你穿起来更好看!”男人们一致同意。
两个小女孩和我一起玩层层叠。最小的跟着一只可爱的猴子,它有粉红色和橙色的腿。他们的妈妈在有人留在营地的沙发上密切注视着他们。一个小时后,她睡着了。她从南苏丹出发只用了三个月。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我们来到了配送中心外一个比较安静的取水点,清洗淋浴间。在这里,森林环绕着一块没有围栏的田地。
边缘已经竖起了一个结构:一个鸽子的鸽舍,被防水油布整齐地包裹着。大路的对面有一家化工厂。
“几年前它泄露了氯气,”一位同事说。“警察让营地里的每个人都离开。有很多人来找我们,眼睛和皮肤都发痒。他们要去哪里?”
三个阿富汗人在淋浴间等着我们打扫干净。其中一个留着尖胡子,穿着红色足球衫,很高兴知道我说法语。我们开玩笑说谁更流利。
他对他妻子说了一句猥亵的话,并递给我一支烟。当我试图对这种慷慨表示敬意时,其他志愿者都忍不住笑了。一辆警车开过来给我们拍照。
我问那个人鸽子收容所的事。“这不是我的,”他咧嘴笑着说。“是伊拉克人!”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。”我们看着鸟儿争抢空间。
许多难民营里的人已经等了好几年,等待在德国处理庇护申请——足够长时间来学会德语。他们看到我的金发就试了一下。
“我在德国住了七年,”一名男子解释道。他身材高大,穿着牛仔夹克,头发两边剪短,头顶留长,扎着马尾辫。他在伦敦的任何一条街道上都很合群。
“我从来没有被允许找工作,”他说,并有些令人吃惊地补充道,“我发现我的朋友都是纳粹。所以我来到这里。”他是新来的。他问哪里可以买到毯子,但今天是银行假日,许多通常的慈善机构都无法提供。
“很抱歉,”我告诉他,“你可以明天去另一家慈善机构登记,但他们要到第二天才能带来任何东西。”
下了一夜大雨后的第二天,我见到了他。“那只是一个晚上,”他说。“明天,我会说:这只是一个晚上。”
随着时间的流逝,越来越多的家庭来到这里,他们受到8月份承诺的在平静的海面上更安全过境的诱惑。我和一对夫妇交谈,他们也轻声请求帮忙找帐篷。我拿出一张有电话号码的卡片:“他们会帮助你的。”
那个会说英语的人看着卡片,一动也不动。“我的手机掉进海里了,”他说。
他解释说,他们离开的那艘船被法国警察击穿了。他们把所有的钱都付给了一个走私者,让他把他们带过去,但走私者会发短信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到船上,现在这对夫妇已经失去了联系。
没有证件,就找不到工作。这个男人不想让他的妻子在营地洗冷水澡,因为她可能会生病;她怀孕了。
“我很抱歉,但你得等到明天做衣服的慈善机构来了,”我说。我很难直视他们的眼睛。
我回到车上。一群年轻人紧跟着我。我以前和他们谈过。戏谑通常是礼貌的恶作剧。不是今天。
“你有吃的吗?”他们问。我回答说:“他们明天两点来。”
“牙刷吗?”“对不起。我们什么都没剩下了。明天还会有更多。”
“吉列吗?”他们会做一些暗示剃脸的动作。“我们都发了。更多的明天。”
一个年轻人靠在货车上。昨天我教他朋友一些法语时,他笑了。他盯着我。“永远是明天,”他说。
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打发时间。我们这些志愿者会抽出10分钟的时间和一些爸爸和他们的孩子一起踢足球。
一个不到两岁的男孩光着脚在砾石和沙子上跑来跑去,高兴地尖叫着。他冲过石头,就好像石头不存在一样。我扫视地面寻找玻璃。他把球抛向我。
我们回到捡垃圾的时代。我们把箱子搬到当地的垃圾场去倒垃圾,怀疑那里是否有空间。只有当垃圾堆积到工业垃圾箱大小时,垃圾收集工作才会开始。
“嘿!”我迅速转身,准备进行一场复杂的谈话,但两个阿拉伯人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箱子。他们帮我们搬。我们走在后面,心存感激。
一辆警车在我们旁边缓缓驶过,一名警官的胳膊像卡车司机一样搭在窗台上。他和他的同事透过墨镜对我们傻笑:“?a va?”他们开走了。
我们盯着道路,不只是为了警察。英国的种族主义骚乱已经演变成慈善群聊,这些群聊分享了一些人的截图,他们承诺要把暴力带到加来和敦刻尔克。挂着英国牌照的面包车载着记者和普通市民在营地附近爬行。我们都很紧张。
很难说为什么大synthe的人选择英国作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地。许多人希望与家人或朋友团聚。另一些人则学会了英语——这是一个帝国的遗产,它引发了许多暴力,现在迫使他们逃离。
有一件事是明确的,这不是为了索取利益。“这里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说过福利国家,”一位同事告诉我,“而那些听说过的人,也从不指望它适用于外国人。”
住在英国酒店的寻求庇护者每周可获得8.86英镑。公交车票、校服和药物都加起来了。他们不被允许工作。
在我的最后一天,下雨了。我记得艾米莉亚离开时说的话:“我不想让人们看到我走了,想起他们被困在这里多久了。”
我留下的志愿者队伍很少。大多数业务在9月前会暂停一周,让正式员工休息一下。到那时,Roots将在营地里运行热水淋浴设施。错过这个我很难过,但很高兴能在牙刷用完之前离开。
我不是唯一一个离开的人。最后一周,由于天气晴朗,过境次数增加了。
上世纪90年代,一家英国庇护中心在安全的加来运营。英国退出是为了削减成本。人们希望,在政府换届后,这种情况会恢复,但这里没有人屏息期待情况很快会有所改善。
第二天,我乘渡船去多佛。我住在法国,在英国期间必须申请新的法国签证。
终点站有个人想借一部电话。另一名年轻的白人男子咧嘴笑着,挥舞着他的手机:“对不起。免费。”我献上我的。
朱利叶斯是捷克公民,已在英国定居,但被拒绝入境。等了一夜,他的手机和钱包都被偷了。他不能再买一张船票了。
我帮他打电话给家人,并充当终端工作人员的翻译。我问过的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被拒绝入境。
公共汽车来带我去渡口。朱利叶斯刚通过我的手机联系到一个人。当他们看到我拖着脚时,另外两个乘客催我走。朱利叶斯抽泣着把手机递了回去。我自己身体也不太好。
抵达多佛后,我排队等候护照检查。一位官员对站在父亲身边的两个法国孩子讲话。“Bienvenue en Angleterre,”他说,他的英国口音夸张了。
一个男孩回答说,他的声音太小了,听不清。这位官员扬起了下巴。“说英语,孩子!”他说。“你在英国!”
相关文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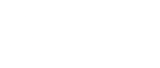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